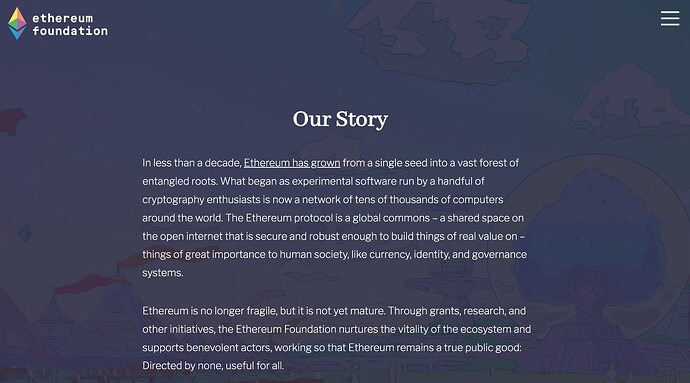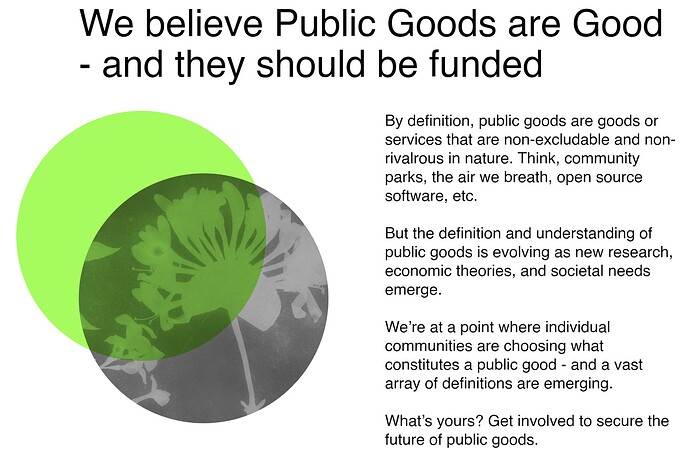嗨,我在修改去年底写过但没发布的一篇文章,和公共物品有关。今天想把第一部分发出来给感兴趣的大家看。谢谢你们任何形式的阅读和反馈!
与“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相比,“共有地(Commons)”不是更合适的术语吗?
我想先引用 Michel Bauwens 的一条推文:
我一直对以太坊和区块链社区使用”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一词感到困惑。它们显然不是来自公共部门的物品,在我看来,它们实际上是“共有地(Commons)”。有人知道为什么选择这个术语吗?
在评论中,Bauwens 进一步阐释了他对物品的三个分类:由市场提供的“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国家和类似国家的公共机构提供的”公共物品”,以及由在地社区集体管理的“共有地”。
从 Bauwens 的框架出发:以太坊由大众自发形成的社区所创建和维护,它显然是“共有地”,而以太坊实际上也没有提供国家通常提供的“公共物品”(公共教育、医疗、国防等等)。为什么人们选择使用“公共物品”这个术语,而不是“共有地/共有地物品(Commons/Common goods)”?
模糊,但被广为接受的“公共物品”
在这条推文下,以太坊中一些有名的“公共物品”倡导者进行了评论,但好像没有出现合适的答案。
Kevin Owocki 的评论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角度出发去判断公共物品:
我认为,对于任何使用以太坊的人来说,网络安全 + 客户端开发团队软件输出等都是公共产品。 (例如,它们以非竞争/非排他的方式使网络的所有用户/读者受益)。
可是,对于那些网速受限甚至无法连接网络的人群呢?“所有用户/读者”指的是那些能够自由接触全球互联网的用户,并且钱包里有以太币(至少目前而言)。如果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一个连续光谱,那么到什么程度,某个物品可以被看作是公共物品呢?
Trenton Van Epps 同意 Bauwens 对于公共物品和共有地的区分,并认为以太坊协议层是自我管理的共有地。但他也没有回答“公共物品”在以太坊社区中的广泛使用:
我同意!与外部参与者提供的公共物品相比,基础层软件更接近于自我组织的共有地,参见 @ProtocolGuild 中的一些工作。
当时我也刚刚参与了一项以“公共物品”为主题的写作(《Web3 公共物品生态研究报告》),“什么是公共物品”是我们在开始写作时就在思考的问题。后面写作过程发生的争吵中,总是绕不开这个问题。
图片截自 telegram 聊天
此外,志在以太坊社区建设”公共物品” LXDAO 也不时会看到这个问题。
在社交媒体上,我也会不时看到一些与“公共物品”有关的担忧,如 Martin Köppelmann 的评论。
依据眼见的零散表达和个人感觉,我以为以太坊社区中对“公共物品”概念的常见困惑可以分为两类,如果你也有些共鸣,那就太好了:
- 对“公共物品”的一般性理解太过宽泛,以至于”公共物品“一词所传达的意义相当模糊,或者说分辨率很低,我们很难去分别什么是公共物品,什么不是;
- 当前许多所谓的“公共物品”在以太坊社区中并没有什么正统性。
第一个困惑与定义有关:在以太坊社区中,“公共物品”这个概念自相矛盾——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但也没有这样的物品。以典型的公共物品——国防——为例:某个国家的国防对于自己的国民来说是公共物品,但对其它国家也许是公共恶品。去理解这个矛盾的一个视角是,在这个概念诞生的 1950 年代,物品通常不会超越国族的边界,我们今天所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在学术界(这个术语通常可以追溯到 1954 年塞缪尔森的文章),这个定义从一开始就有争议。Michael Pickhardt 追溯过从萨缪尔森开始的“公共物品”概念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年(1955),在其它学者的回应下塞缪尔森修改了原始框架,承认许多政府活动旨在提供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物品(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建模距离现实太过遥远!)。
在 Michael Pickhardt 的叙述中,之后,对于“公共物品”的定义,经济学家基本上走了两条路:一条是从制度角度看待公共物品,认为公共物品本身并没有某种本质性的特征,而是制度性的。在这里我把制度理解为集体选择的过程和结构。简单来说,人们一起决定了什么是公共物品,什么不是,例如医疗、教育在某些制度下应当被全部免费提供,在一些制度环境中被看作是可被部分私有化的服务。
另一条则沿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框架,但将公共物品放在一个渐变的光谱上。
在以太坊中,这种模糊性也有影响。模糊的定义与经济激励(以太坊生态的大量资助项目)结合后,“公共物品”成了一个模因:它太宽泛了,因而允许具有不同动机的组织和个人将其作为“叙事”,参与各个资助的竞争或吸引投资。多用例子吧。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些项目可能声称自己是“公共物品”,但只是为了积累个人资本或小群体的利益,这导致了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正统性。如 Trenton Van Epps 所说:
按照 Vitalik Buterin 的说法,正统性(Legitimacy)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接纳”。更高层次意味着这是集体的,不是某个个人的接受,而是一种社会规范。我能理解一些 buidler 的不适——“不纯粹的公共物品”这个类别太宽泛,他们也真的不想将自己在做的事情与其他一些“公共物品”项目放在同一类别中。
但我们对公共物品有一种集体性的期待,对吗?在以太坊社区中它也许不像“去中心化”那样明确,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达成某种最广泛的共识,否则就不会有这么些人(也许包括你)对“公共物品”的使用感到不适。而我们需要在社区中进行公开的、彼此尊重的对话,以建立这种共识。
这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试图为那些对这个术语以及它所指代的对象感到困惑的人进行些一些澄清,提出一些问题,并希望能够开启一场对话。如果我们对“公共物品”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和共识,我们也会更了解要一起去向哪里,思考要一起如何行动。